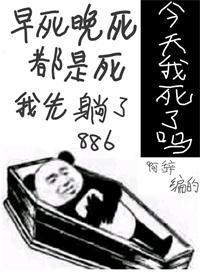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第十九章 努力按捺的向往(第1页)
随着姚易青的离开,宫安沫硬撑着的身体如开口的气球陡然萎缩,肩膀的颤抖,背影的摇晃。姚易青的宣告如千斤重的巨石落在宫安沫的身上,双腿几乎无力支撑孱弱的身躯,宫安沫死死地握住饭桌边缘,稳住自己的身体不颤抖。
‘我们分开吧。’五个字如五根生铁铸就的坚硬钉子钉到宫安沫柔软的心脏,如一把锋利的斧头切断宫安沫的人生,如一阵席卷一切的狂风把她赖以立足的过往连根拔起。
前尘往事纷乱焦躁地映现在脑海,待宫安沫试着去抓住具体回忆的轮廓时,却如戏弄盲童的坏心同学转身溜走,无影无踪。透过朦胧的泪眼,宫安沫看见橱柜玻璃上映出的自己的面容,影影绰绰,如同隔了多年回忆。
死命的咬住下唇,封住如洪水冲撞四处寻觅出口的呜咽,姚易青说过不要在她面前流泪因为眼泪是最廉价的,可是为何就是止不住眼中的泪水夺眶而出,流过脸颊、嘴角,在下巴汇聚,汇合下唇被咬破沁出的血,滴在手上,触目惊心,流进水池,无声无息。
她今后的生命中不再有姚易青!原来一切可以变得更坏,生命的最后一段有她陪在身边此刻也成了遥不可及的奢望!因为她刚刚的宣告,只剩下有限生命的噩耗竟没有之前那么沉重,对于宫安沫来没有姚易青的生命也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
从最初听到姚易青的宣告到此刻,宫安沫唯一能思考的唯此而已,像不会游泳的人被卷进旋涡里,所剩的唯有寻找呼吸。‘早上不会有她一起早餐,晚上不会有她同床而眠。从今往后的漫长人生中,眼睛不会再有她的身影、面容,耳边不会在听到她的声音,呼吸间不会再有她的记忆。’想到此,宫安沫心口一阵刺痛,手抚上心口,如扑火的飞蛾,徒劳地想把支离破碎的心归拢到一块。
泪眼朦胧中宫安沫看向书房门紧闭,想象着被坚固的墙体隔绝在另一面的姚易青,眼泪如泉水从从泉眼中翻出,宫安沫努力的压制,不受控制的一声呜咽溢出嘴角。周围的空气愈来愈稀薄,更担心姚易青发现她在哭,宫安沫穿上外出的长款羽绒服,换上棉鞋,如同逃亡一样急急地出了门。
十二月的夜晚,天色越晚越觉得寒气逼人,小区里行人稀少,偶见一个晚归的人也是形色匆匆,缩头躲避寒风钻进衣衫里,匆匆低头走过。
宫安沫走到小区中央的小公园里,小区里的健身器材冷冷的孤独站立着,给小孩子玩的沙坑、滑梯上空无一人,在清冷的月光和昏黄的灯光中,更显的形单影只。上玄月低低地挂在树梢,城市里的月亮失去了存在的空间,高楼大厦遮挡、霓虹灯光弱化,很少会有人抬头看或者意识到它的存在。宫安沫回想起小时候在农村生活时,满月的夜晚,亮白的月光将天地照亮,一切介于白昼与黑夜之间。而此刻的月亮似不得不在寒夜站岗的哨兵,瑟缩着履行挂在天上的职责。
人类繁衍生息一茬又一茬,不过区区几十年而已,而月亮却是亘古不变,并将存在下去。在永恒的不变面前,各种各样的变又算的上什么。宫安沫心想,我现在30岁,也许再过50年,我已化为尘土,站在终结点往回看,至于度过怎样的人生又有什么意义呢?有姚易青的人生与没有姚易青的人生又有何区别呢?宫安沫抬头望着月光,清凉的光照在脸上与闪闪的泪痕结成一片。宫安沫比谁都清楚,这样的假设问题,万念俱灰之下选择虚无主义是可笑的自欺欺人,她真正的人生是伴随着姚易青的到来开始的,也将随着姚易青的离去而告终。
对于两人、关于未来,在今天之前宫安沫一直是矛盾的,是不安与满足共生,是想要与退缩交替。爱着她却不敢太靠近她,爱她到骨血里却不敢让她知道,想要与她长相厮守却从不敢流露半点的纠缠,明明与她分开是最不愿意的事却装作若无其事地接受,甚至于问原因的资格都没有……只因为,宫安沫明白姚易青不爱她,而姚易青也早已明白的宣告,两人的维系只在于十年前的一纸契约,而她有权可以随时终止。
十多年生活在同一个空间,朝夕相处,宫安沫刻意忽略那一纸契约,暗暗希望可以一直陪在姚易青的身边,即使……即使她不爱自己,也许一辈子都不会回头看身后的她一眼,也无所谓。一切在今天戛然而止,背后的原因,宫安沫不敢问,对于早已明明白白预设的事,追问又有何意义呢?况且……姚易青会烦。
寒风吹在满布泪痕的脸上,硬生生的疼,没有手表和手机,宫安沫靠着廊柱,不知道坐了多久,只觉得通体冰凉,明显地感觉到衣服的触感。周围没有人声唯有风摇动光秃树梢的声响。擦干眼泪,宫安沫欲站起身,双脚骤然传来一阵麻木刺痛感,待麻木平复,宫安沫站起身,朝家走去。
姚易青洗好澡,倚在床上看书,已经10点半了,她还没回来,打了电话,没人接,下床来到客厅放发现手机在餐桌上嗡嗡作响,知道她没带手机出门。
按灭电话,回到床上继续看书,眼睛一行行地扫着书,姚易青的注意力却为听觉所掌控,留神细听客厅里的声响,书一句句看在眼里意思却散了,不知道读的什么。有开门的声音传来,不知为何,姚易青赶紧放下书,关了灯,假装睡着。
黑暗中,感觉变的特别敏锐,姚易青静静地躺在床上,察觉到宫安沫小心翼翼地进来,拿了衣服又出去,接着浴室里传来放水洗澡的声响,久久地,姚易青都已快睡着时,宫安沫进来,在床的另一侧慢慢地躺下,床垫微弱的晃动带来夜的心安,姚易青沉沉进入梦乡。
姚易青从睡梦中醒来,梦与现实的界限还混合在一起,似听到有细碎的□□和微微的颤动。打开床头灯,时钟显示凌晨2点,姚易青意识渐清醒,回头看见身侧的宫安沫眼睛紧闭,细碎的发丝润湿着黏在脸上,头随着身子痛苦的无意识扭动。
“安沫,你怎么了?”姚易青坐起身,手摸向宫安沫的脸颊,汗的潮湿与皮肤的冰凉从指尖传来。听到姚易青的呼唤,宫安沫用力的睁开眼,“嗯……”,她有气无力的虚弱应道,不及看清楚眼前的场景,又无力的合上,再次被拉回黑暗中。
“安沫——安沫——,你醒一醒。”姚易青跪坐在床上,摇动宫安沫的肩膀,宫安沫汗湿的头前后摆动,见她依然不清醒,姚易青心急如焚,决定要立即去医院。’
姚易青急忙将宫安沫汗湿的睡衣换下,再七手八脚的给她穿上厚的棉服,姚易青也换了衣服,找到宫安沫的医保卡,拿着手机、车钥匙,搀扶着她出了门。
凌晨的急救门诊,带着夜的倦怠又掺杂着难料的危急。醉醺醺的中年男子磕破了头,缠着白色的绷带,头向后仰躺在椅子上,身边大概是他老婆,不安地低声哭诉着,“让你少喝点酒,你偏不听,还骑电动车,你说说,你要有个三长两短,我和孩子……”男人不耐烦地哼哼着,不知听进了多少。
医生和护士也是意兴阑珊,表情巧妙地融合了随时准备迎接紧急状况的紧张和都别来烦我的不耐烦之间,人来人往的每个人脸上如蒙了一层灰色的纱,扯不断理还乱,一切都带着专属于后半夜的疲惫和不真实。
姚易青坐在急诊室门口,等着医生诊断完出来,虽然接诊医生初步判断,可能是受了凉应该没有什么大碍,姚易青还是觉得不放心。
‘和昨晚的事有关吗?’姚易青心里想,却没有答案,也许宫安沫并没有她表现出来的那般平静地接受分手的消息。宫安沫心里是怎么想的,她一向很少表现出特别的情绪,安静的像空气,偶尔会让人忘了她的存在。而两人也很少谈心,姚易青不问,她也很少说,仅有的交流,多是日常事务性的沟通。‘你几点到家?想吃什么?什么东西在什么地方之类’。
姚易青明白她和宫安沫在一起,尽管已经十年,却并不爱她,至于为什么共同生活了十年,姚易青觉得原因在于惯性,在没有突然的外力作用时,一切总是被吸附在名为“稳定”的轨道上,自己也和多数人一样过着谈不上绝望也没有希望的生活。
对于骤然的分手决定,姚易青并不像表面的那般冷漠,毕竟十年的朝夕相处,并没有什么不愉快的记忆。然而拖拖拉拉,不是姚易青的风格,手起刀落的阵痛好过拖泥带水的纠缠,分手必须的而且紧迫的,关乎原则和渴望。
急诊室的门开了,医生出来,身后跟着护士推着独轮床,宫安沫躺在上面,身上盖着白被单,姚易青迎上去,“医生,她怎么样了?”
“没什么事,可能是精神波动太大,又受了风寒。”医生停下脚步,取下口罩,“等醒了可以直接回家了,要是不放心,也可以在医院输一些营养液,观察一下,明天再出院。”
“好的,谢谢,还是明天再出院吧。”
宫安沫躺在病床上,还没醒来,姚易青拉上布帘,找了一把椅子坐在旁边。不知是医院所处可见的白墙、白被的映衬还是白色灯光的反照,沉睡中宫安沫的脸异常苍白,眼睛似有些肿,鼻子也红红的。‘她哭过了吧。所以才那样憔悴。’凝视着宫安沫的脸,姚易青心里渐渐浮现出异样的感觉,有别于愧疚的另一种情感,似站在沙漠里眺望落日时空寂的疼。
宫安沫的眼角似有光在闪烁,姚易青以食指轻拭,指头氤湿,灼的姚易青慌忙缩回手,多久了,记忆中宫安沫不曾在她面前流过泪,因为在梦里所以才会流泪吗。
“还没醒吗,我来测下体温?”人未到,声音先到,值班护士拉开帘子进来,大概四十多岁,个子不高身材微胖,声音爽朗,手脚麻利,随和、专业汇合成让人安心的形象。
“一直没醒,没事吧?”姚易青起身担忧地问。
“医生看过都说没事了,不用担心。”护士仰头望着吊水架,“这一瓶快输完的时候,喊我。”护士朝远处的护士台呶呶嘴,“呐,就在那边。”
“没事的,别担心。”护士读着温度计指数,填在纸板上,“体温什么的也都正常。”
“嗯,谢谢。”
宫安沫睁开眼睛,白色的空无一物的屋顶,四周环绕着白色的布帘,视线下移,映入眼帘是姚易青坐在椅子上趴在床沿睡着了的身影。
‘那样的姿势睡着青肯定很不舒服吧。’宫安沫心里想着,恍惚似做梦一般。这里是哪儿?宫安沫试着支起身子观察四周,细微的动作惊醒了姚易青,姚易青抬头,见宫安沫醒来。“你醒了?”
“这是哪里?”出声才发觉,自己的声音干涩沙哑,喉咙微微的发疼。
“医院。”姚易青站起来将枕头立起,扶着宫安沫靠着,“你昨夜高烧昏迷。”
诸天演道
关于诸天演道当现代都市里出现打人如挂画水不过膝。当国术江湖里出现徒手抓子弹神掌天降。当武侠江湖里出现敕鬼驱神摧城搬山。当末法时代里出现天地灵气长生物质。别人练武,吾修仙。别...
剑守长安
二十一世纪的李剑白,来到异界神州长安。李剑白莫名其妙成为唐国六皇子,本想做个逍遥闲王,仗剑天涯,游历江湖。可正逢唐国内忧外患,李剑白不得不提剑而起,一人肩负重任。我有一剑,守了长安,护住唐国,安得天下,庇护人间。我有一剑,逆天而行。诛仙,弑神,定九州,安世间。剑与痴情皆不负!...
盲妾如她
俞姝眼盲那几年,与哥哥走散,被卖进定国公府给詹五爷做妾。詹司柏詹五爷只有一妻,伉俪情深,因而十分排斥妾室。但他夫妻久无子嗣,只能让俞姝这个盲妾生子。他极为严厉,令俞姝谨守身份,不可逾越半分。连每晚事后,都让俞姝当即离去,不可停留。这样也没什么不好,可惜俞姝眼盲,夜路无法感光,总是摔得遍身是伤俞姝没有怨言,谨言慎行地当好一个妾室。她只有一个念头等她兄长造反了这定国公詹五爷忠守的朝廷,救她出囹圄!但她怀孕了。又在生下孩子后的某天,亲耳听到了詹府对她的决议留子去母。俞姝当即逃走,五爷的兵马铺天盖地地寻她,终于把她堵在山崖。那天山崖风很大,将她吹得翩然欲飞。五爷指尖发颤,声音嘶哑,阿姝,不是你想的那样你下来,我们好好说说话,行吗?俞姝不懂,他怎么能把哄骗的话说得如此悲切?然而无论如何,她不会再留他身边了。她朝他一笑,在他目眦尽裂扑来前,纵身跃下三年后,虞城王拥兵自重,招天下名医为胞妹治疗眼疾。詹司柏听闻,发疯似的狂奔而去,看到了那位重见光明的王姬。王姬眼眸清亮如明月,笑着问候他。许久不见,五爷与夫人可好?1v1sc狗血古早风,不喜勿入。男主夫人非他真正夫人。预收宫阙春深阮茗永远闭了眼睛,在漫天大雪的深宫里。她因爱慕永熙帝进宫,又为永熙帝挡箭而死。死后魂魄飘在半空,她才看清了一切。她所谓的奋不顾身救驾,不过是永熙帝平衡朝堂玩弄权术的手段罢了。皇帝不会伤心,伤心的只有疼爱她的爹娘哥哥。她终于懂了,这皇宫如巨大的深渊吞噬着人心,没有温情也没有爱意。于是她拼了命地逃离。重生后,见到爹娘哥哥,阮茗发誓再不进宫,只与家人过平安喜乐的日子。她准备和青梅竹马的英国公世子成亲,就此开启新的人生。可定亲那日,却被生生掠去宫中。男人身上熟悉又陌生的气息笼罩着她。他将她抱坐在御书房的书案上,俯身将她圈住,使她无处可躲。那眸中如有不可抗拒的旋风席卷着阮茗。阮茗颤抖,他却笑着捧起了她的脸。阿茗怎么变了?不愿进宫来陪朕吗?朕等你很久了一个痛醒的小姑娘,一个缺爱的偏执狂皇帝不死心塌地地捧出真心,小姑娘不会爱他。酸甜口苏爽文,架空勿考据...
帝宠绝色星蕴师
这摸也摸了,亲也亲了,就罚你以身相许吧!本尊的便宜,可不是那么好占的!他,一袭白衣,拥有绝世美颜,位高权重,唯独宠爱一个人人不待见的小丑女。她,夏家孤女,人人唾弃的废材丑女,一朝穿越,名震五行大陆。初次见面,她从天而降,看了他的身子,偷了他的裤裤。再次见面,堂堂大国师却被小丑女占尽了便宜。某女双手环胸国师大人?我这一马平川的小身板,恐怕引不起你的兴趣吧!你这上下其手,难不成你有恋童癖?某男邪魅一笑本尊只是摸摸你的根骨而已,别幻想本尊会对你有意思!他们是人人羡慕的眷侣,也是天生的欢喜冤家,几月的恩宠,千载的纠缠,竟为这一世的恩怨重逢。泡美男,戏神兽,我的穿越我做主,神器丹药在手,美男跟我走!...
我在六扇门当差的日子
我在六扇门当差的日子是江户川东南精心创作的灵异,旧时光文学实时更新我在六扇门当差的日子最新章节并且提供无弹窗阅读,书友所发表的我在六扇门当差的日子评论,并不代表旧时光文学赞同或者支持我在六扇门当差的日子读者的观点。...
今天我又被迫复活
文案顾绒能够死而复生。从他意外身亡第一次开始,他每次死亡都会复活。以前算命的说他命不好,得取个软点的名字,不然死得早。顾绒不信,非改了名,第二天他就因为屁股疼,在去医院的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