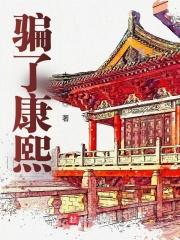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分卷阅读58(第1页)
人已经不再需要什么理由。”两人的地位差距已与从前大不相同,白鹤庭心里清楚得很,但他疲于思考这些头疼事,只应付了一句:“我顺着他的意就是了。”他抬手揉了把脸,又把那只手放于面前,摊开了手心。他怔怔道:“我的手上,有他血的味道。”距离骆从野被救走已经过去了半个多月,白鹤庭的手上不可能还残留着骆从野的信息素,他所闻到的大约只是在标记影响下与龙舌兰酒交融的冷杉味道,但苏幸川没有反驳,只说:“我喊人给您接净手的水来。”白鹤庭摇了摇头:“不用了。这个味道,能让我舒服一点。”那张纸每每被压平,又很快再次皱起,他放弃了与那纸较劲,低声问:“苏先生,你说,他死了吗?”苏幸川道:“他身上没有致命伤。他是个年轻的alpha,那点皮肉伤很快就会愈合的。”白鹤庭抿紧唇,沉默地回忆着自己刺向骆从野的最后一刀。腹部是既安全又脆弱的位置,下刀的位置与角度稍错一点,人就有可能有性命之忧。可落那一刀的时候他手抖了。他不确定自己有没有伤到骆从野的脏器。如果时光倒流回那个雨后的清晨,他一定让骆从野毫无痛苦地死在自己怀里。“我是不是做错了。”白鹤庭喃喃地问。“如果您不那么做,那他之前所受的苦就全都白受了,所有的努力也都会功亏一篑。”苏幸川安慰道,“不要责怪自己,被您这样强大的人爱着,他已经很幸福了。”“爱?”白鹤庭转过头来,愣愣地看着苏幸川。爱,这个词,在那个被柔光笼罩的清晨,骆从野曾对他说过许多遍。他还记得他说“我爱你”时的语气。他的嗓音很柔软,有一些沙哑,但字字清晰。他还记得他严肃的脸,专注的眼神,和怀抱里的温度。骆从野是第一个对他说爱的人。白鹤庭用双手撑住桌面,缓缓垂下头,迷茫道:“什么是爱?”好容易捋平一点的纸又叫他抓皱了,“我爱他吗?”从十一岁到二十八岁,苏幸川亲眼看着白鹤庭由一个倔强孤僻的少年,成长为一位无坚不摧的将领,但他从未见过他这般彷徨。他甚至觉得,此时若吹来一阵风,白鹤庭便要散到那风里去了。苏幸川慢慢地叹出了一口气。“爱就是,”他轻声道,“滴落在您名字上的那滴眼泪。”白鹤庭一怔,猛地看向自己手下的那张棕色纸。黑色墨迹已经晕开了一点。那滴泪落在纸上,像他名字上面的一块伤疤。他还未来得及反应,另一滴泪也坠了下来。白鹤庭抬手抹了一把脸,为自己的脆弱而感到羞愧。他突然意识到,距离自己上一次落泪才过去没多久。上一次也在这里。他想起了那片漆黑,也想起了那个意乱情迷的吻。他强迫自己收回思绪,在几张空白纸张下面找到了一个巴掌大的亚麻布袋,又在布袋中发现了一颗圆滚滚的珍珠。是他从南方带回来的那一颗。白鹤庭扬了扬唇角。这大约就是骆从野遗憾带不走的东西。布袋下面则是一本书。他取过那书翻了翻,惊讶地发现,那书竟是一本外国诗词的手抄本。才翻了几页,一张夹在书中的纸便出现在了视野里。这张纸曾被他团成了一个纸球,如今倒被压得平平整整,上面写着——“你站在那儿做什么。”
但他的视线没有在自己的笔迹上过多停留,很快被那一页的一首诗词吸引走了全部注意力。那是一首他很熟悉的诗,有人在这首诗上搞了破坏——“嘉树鹤庭宽”的“嘉树”二字被人用黑色墨水涂掉了。“幼稚。”白鹤庭摸了摸那块干涸的墨,轻轻地笑了。“所以,他才不喜欢这个名字。”不自觉地,白鹤庭向后退了一步。他看到骆从野翻开那本诗集,一脸不高兴地划掉两个字,待墨汁风干后,又把那张被团成过球的纸展开,压平,夹进了书里。他还看到骆从野从衣袋中掏出一颗雪白圆润的珍珠,小心翼翼地收入到一个材质低劣却崭新干净的布袋里。他甚至听到了一声像风一样的轻唤,沙沙的声音温柔地擦过了他的耳膜。“我爱你。”他的嘴唇还留有那个吻的触感,那个带着决绝意味的,蜻蜓点水的吻。骆从野给了他一个吻,他却还了骆从野一刀。白鹤庭的身形忽然晃了两下,苏幸川连忙向前几步,及时扶住了他的胳膊。“您真的没事吗?”老管家的面色已经带上了焦虑。白鹤庭一手捂着嘴,另一手冲苏幸川摆了摆:“胃口不大舒服,大概是吃坏……”他话没说完,胃中一阵翻涌,不由得躬背埋头,作势要吐。他用力呕了几回,长长的眼睫挂满了生理性眼泪,却什么都没能吐出来。苏幸川忧心忡忡地替他顺了顺背:“这几日您都没吃过什么东西,怎么可能吃坏?”又扶着他在床边坐下,说,“我叫人弄点温热的食物来。”听闻此言,白鹤庭的胸口又激起一股呕意,他再度干呕了几下,皱着眉制止了苏幸川:“我不想吃。”说罢,将后脑贴上墙壁,倚靠着墙闭目休息了片刻,待反胃的不适感稍微缓解,才道:“你让我休息一会儿。”苏幸川与他一同安静了下来。房间里静得只听得到白鹤庭刻意拉长的呼吸。过了好一会儿,苏幸川突然问:“这反胃的感觉,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白鹤庭粗略地回忆了一番,倦怠地答:“两三天前吧。”苏幸川又丢出一个风马牛不相及的问题:“您上一次发热是什么时候?”白鹤庭蓦地睁开了眼。他几乎都要忘记了发情期这件事。上一次发情期正是角斗场庆典前的那几日,大约是两个月前。依旧是在这里。他张了张嘴,半晌都没有说出话来,末了,垂着眼道:“是我最近太累了。”苏幸川这次沉默的时间更久了。“嗯。”他低声道,“也许就像您说的,您最近太累了,所以胃口不太舒服。”白鹤庭也陷入了沉默。他们两人都心知肚明,那只是一句安慰的说辞。“就算真的……”苏幸川顿了顿,把后半句话咽进了肚子里。他谨慎地朝房门处看了一眼,用更低的声音说:“等您做完标记清洗手术,它自然就没了。”白鹤庭脸上挂满了吃惊之色:
战神影后
食我安利文案应天国的女将军齐麒在庆功宴上中毒身亡!将军大人魂穿到了一个明星的身上。确切地说,是穿到了一个几乎把圈内人得罪光声名狼藉负债累累过了气的明星身上。齐将军表示很头疼编剧头疼总好过心疼。齐将军表示不想演戏编剧别忘了你欠我的两千万。齐将军表示自己可以当武替编剧既然我推荐你当主演,你就必须当主演。齐将军怒了演砸了老娘概不负责!编剧如果主演不是你,这剧就真的砸了。...
骗了康熙
...
天才萌宝,总裁爹地放大招
一场阴谋,将她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未婚夫的抛弃,亲人的背叛,一夜之间她成了一无所有的人,从高高在上的千金小姐沦落成全城笑话,狼狈至极时,她逃离出国。再归来时,恋雨柔的身边多了一个腹黑的天才萌宝。萌宝联合他的总裁爹地放大招,把曾经欺负过他妈咪的人,通通欺负了回来。恋七七爹地爹地,那个坏女人骂妈咪是狐狸精!冷爵杀放肆,掌她嘴!恋七七爹地爹地,最新情报,有个叔叔亲了妈咪一口!冷爵杀是谁那么大胆,我去灭了他!!!冷爵杀把恋雨柔宠上天宠入地,宠到愿意为了她与世界为敌。...
提刑大人使不得
为保住家产,遗腹子慕流云女扮男装二十载,只想当一个平平无奇的司理参军,招招猫,逗逗狗,破破冤案,顺手再解救几个无知少女。可是一不小心,怎么小辫子就落到了活阎王手里。慕流云提刑大人,查案就...
六零吃饭嫁人养娃
(20号入v啦,每天下午六点更新,笔芯)安样作为一个末世基地的高级厨师,被连累死在一场大型丧尸战争中。她再醒过来,就是缺衣少食的六零年。大湾村刚刚经历过一场山坡坍塌,有不少人因此死了,安样家的人都没了。...
藏锋
太子弑父,天降灾祸饿殍遍野。乞儿命苦,数九寒冬家破人亡。是谁说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是谁说善恶有报因果轮回?尽是荒唐!弱肉强食,何来道义!物竞天择,何来公平!...